法厄同(Phaethon)贸然迁走太阳神的车,驾驶它遨游在天地间,但他又怎是好驭手,须臾之间,马车脱离了法厄同的控制,大地为之灼烧,幸好宙斯赶来救场,但可怜的法厄同被宙斯狠心击死,最后坠入波河。尤瓦尔·赫拉在《智人之上: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》(Nexus: A Brief History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from the Stone Age to AI)开篇利用这个神话故事教训人们,永远别去召唤自己控制不了的力量。人工智能就是这样的力量。约书亚·本吉奥(Yoshua Bengio)、杰弗里·辛顿(Geoffrey Hinton)、山姆·奥特曼(Sam Altman)、埃隆·马斯克(Elon Musk)、穆斯塔法·苏莱曼(Mustafa Suleyman)都警告公众,人工智能可能会摧毁人类文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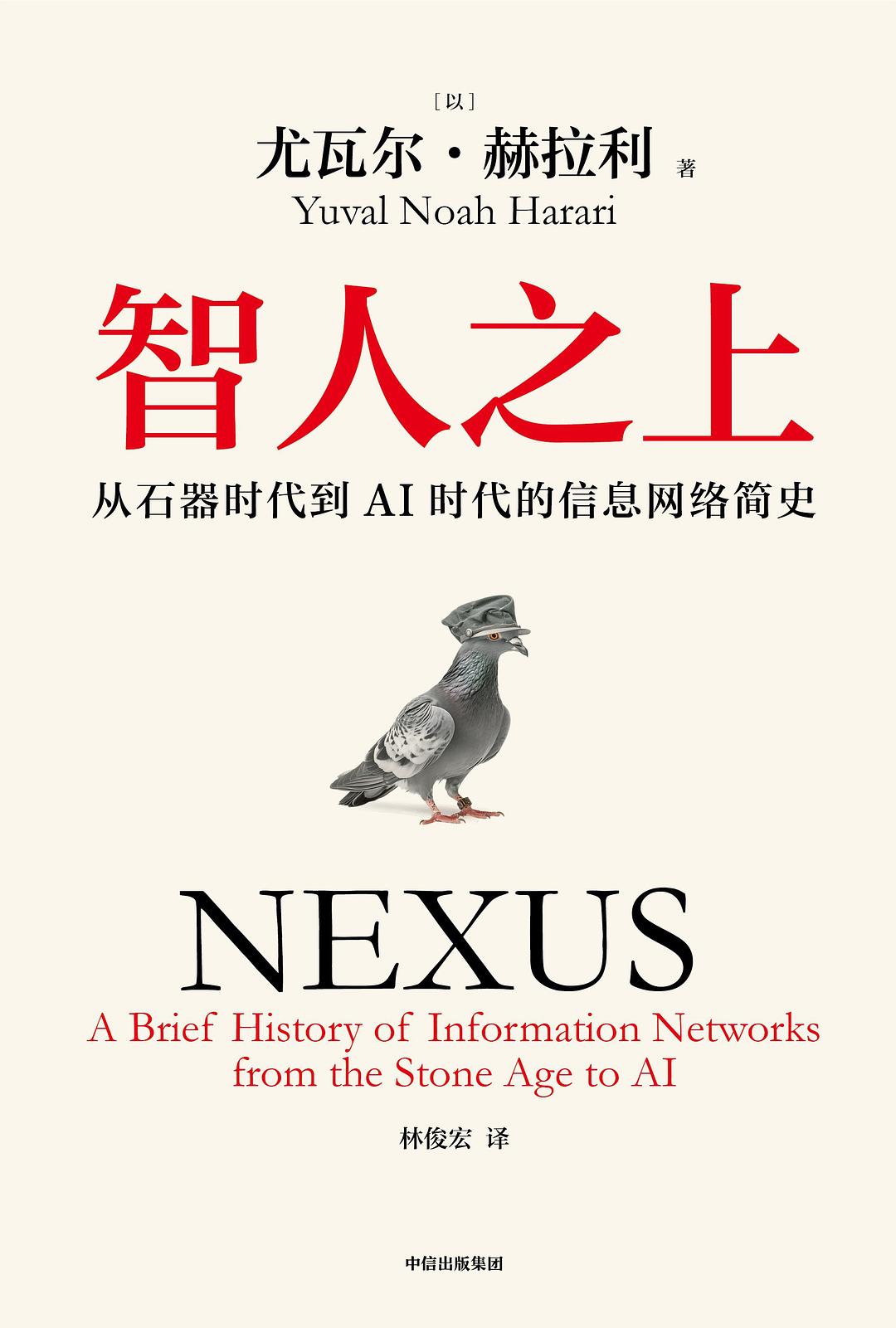
《智人之上: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》
如何改良天真的信息观呢?通过引入秩序,信息不仅指向真相,还指向秩序,它们最终才能形成智慧和力量。尤瓦尔·赫拉利的表述更为晶莹且掷地有声,“智人之所以能成功,秘诀在于懂得运用信息,并把许多人联结起来。但很遗憾,人类拥有这种能力的时候,常常也会伴随着相信谎言、错误与幻想。”随着他的剖析,信息的定义和质感发生了变化,信息仿佛能插上翅膀,且能实现千百种变化。天真的信息观由此演化为复杂的信息观,后者重在人与人的联结,乃至人与故事的联结。
尤瓦尔·赫拉利笔下常见各类名词,比如豪尔赫·路易斯·博尔赫斯《论科学的精确性》、信鸽英雄谢尔·阿米、“十诫”、《新故土》、楔形文字泥版……列举这些名字,不止要说明,尤瓦尔·赫拉利热衷于不同源头的经典文献,还要说明,他筛选和判断信息的能力相当好。像博尔赫斯这样的信息点,其实是诸多系统与叙事的核心要素,换言之,它是河源,它是最大的河。在所有流经人类历史的信息之河中,尤瓦尔·赫拉利总能找到最厚重,最主脉的那个。因此,之于他本人,他既未采信天真的信息观,也未依赖复杂的信息观,而主要施用透明的信息观,即从最好的信息出发,最后再返归最好的信息,前者是务实的,后者是务虚的。
有机体是算法(the organism is an algorithm)。“现在,新的转变正在发生。正如宗教神话使神圣权威合法化,人文主义意识形态使人类权威合法化,高科技大师和硅谷先知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普遍叙事,他们使算法和大数据的权威合法化。这个新的信条可以命名为数据主义(Dataism)。”在2016年发表于《金融时报》的文章中,尤瓦尔·赫拉利写道,“其极端形态是,数据主义世界观的支持者将整个宇宙视为数据流,将有机体视为不多也不少的生化算法,并相信人类的宇宙使命是创建一个包罗万象的数据处理系统,并融入它。”
2013年,戴维·布鲁克斯(David Brooks)在《数据哲学》(The Philosophy of Data)一文首次提及了数据主义一词,戴维·布鲁克斯对数据主义的使用是比较基础的,他认为,充足而正确的数据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预测未来。尤瓦尔·赫拉利的思虑显然更深刻,他洞见道,数据主义正在重新塑造一种权威。如果说人文主义将神的权威瓦解,并将权威建构在个人的感受上,那么,数据主义将个人的叙事扫了一空,权威重新回到了云端。“我们正在培养一种为一个人创造的能力,同时也在培养一种压迫一个人的能力。”尤瓦尔·赫拉利对《诺耶玛》(Noema)表示。
今天不乏技术悲观主义者。埃利泽·尤德科夫斯基(Eliezer Yudkowsky)在去年《时代周刊》的专栏文章中警示人们,如果有人建立了一个过于强大的人工智能,每一个人类成员和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会在不久之后死亡。为防止此事发生,他建议,在全球范围内无限期暂停新的大型训练,并关闭所有大型GPU集群。
尤瓦尔·赫拉利,也会被看作是技术悲观主义者,但也许他更像是技术人文主义者,他企图调和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倾向,同时也强烈地呼吁各界人士关注人工智能及其可能的破坏力,尤其是“美丽新生政”(Brave New Biocracy)的发生。他反复提醒人们,硅谷不了解自己产生的巨大影响,他们对历史、人类社会和人的心理造成了深刻的改变,而人类或许在诸多事务中兑现自己的真正潜力,这个新的图景被他命名为超人类主义(transhumanism)。
虽然人工智能前所未有,但是人类历史上不乏类似的革命,比如认知革命(Cognitive Revolution)、南方古猿(Australopithecus)、自然选择(natural selection)……尤瓦尔·赫拉利总是能够找到某种策略或者框架,讲述这些学术叙事。他最常用的框架是,拿出两个方案与方案,与读者一起比较它们,最终选定一个更优的方案,通常是有点耸人听闻的方案,比如“八卦理论”、“贪吃基因”。有时候他会提出自己的方案,并适时将其升级为大主题,比如他备受争议的农业革命骗局理论。尤瓦尔·赫拉利认为,农业革命使得人类的食物总量增加,但是农民更辛苦,吃得更糟,且产生一群养尊处优、娇生惯养的精英分子。在这个方案中,他甚至提出了一个有些惊悚的论点,他说,“这背后的主谋,既不是国王,不是牧师,也不是商人。真正的主要嫌疑人,就是那极少数的植物物种,其中包括小麦、稻米和马铃薯。人类以为自己驯化了植物,但其实是植物驯化了智人。”智人(Homo sapiens)变成了被几种植物关在房子(domus在拉丁语中是房子的意思)里的物种。但无论如何,人类没有被农业革命所吞没,反而建立了新的食物体系、生态体系,以及智识体系。
为了寻找未来,尤瓦尔·赫拉利不再单纯关注人工智能领域,他叮嘱人们关注生活的世界,以及想象的世界。他引入主体间性,比如法律、神祇、国家、企业和货币,类似女巫,解释力很强,但又很人性。这些主体间的现实,并不是指任何已然存在的事物,而是在人类交换信息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。
早在《人类简史:从动物到上帝》(Sapiens: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)甚至更早时期,尤瓦尔·赫拉利就相当强调主体间性及其重要性。比如他在《人类简史》中论述道,“事物的存在,靠的是许多个人主观意识之间的连接网络。就算有某个人改变了想法,甚至过世,对这项事物的影响并不大。但如果是这个网络里面的大多数都死亡或是改变了想法,这种主体间的事物就会发生改变或是消失。之所以会有事物存在于主体之间,其目的并不是想存心骗人,也不是只想打哈哈敷衍。虽然它们不像放射线会直接造成实质影响,但对世界的影响仍然不容小觑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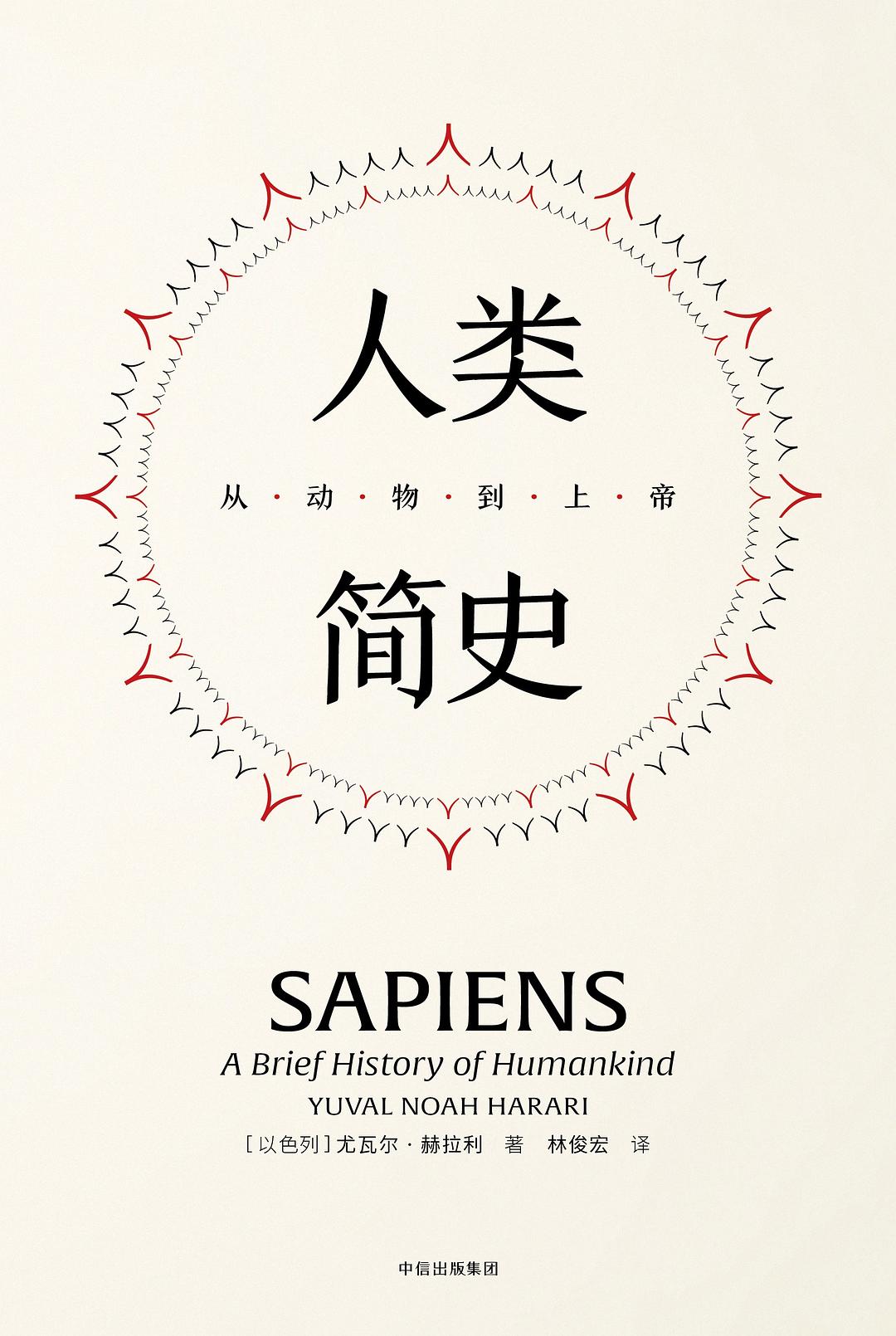
《人类简史:从动物到上帝》
主体间性将尤瓦尔·赫拉利带回了平民立场,他始终关心数字独裁(Digital Dictatorship)可能沦为新卢德主义者的人们。正如尤瓦尔·赫拉利所提示的,目前存在着危险的信息不对称:那些领导信息革命的人,比起那些应该监管它的人更了解背后的技术,在这种情况下,只是一直高喊“顾客永远是对的”“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”又有什么意义呢?而人们正在等待出现在《智人之上》封面上的鸽子,在圣经故事中,鸽子象征着洪水的结束。
2019年,莱斯莉·戴格尔(Leslie Daigle)在一份名为《互联网不变量》(The Internet Invariants: The properties are constant, even as the Internet is changing)的文档中警示,堆栈(stack)的网络结构正在发生变化,它正在丧失独立、弹性、通用性,并正在走向僵化。为此,玛丽亚·法雷尔(Maria Farrell)和罗宾·贝尔容(Robin Berjon)呼吁互联网重新再野化(Rewilding),以避免出现类似“森林之死”(Waldsterben)的局面。再野化取自保罗·杰普森(Paul Jepson)和凯恩·布莱思(Cain Blythe)的同名书籍,《再野化》(Rewilding: The Radical New Science of Ecological Recovery)。
再野化类似于尤瓦尔·赫拉利提出的自我修正机制。不止人类身边的大多数事物,就连人类本身,都是这套自我修正机制的产物。
跟随自我修复机制,人们来到了尤瓦尔·赫拉利提出的三个解决方案:为善;去中心化;相互性。又一次,他将人们带向了充满希望的境地:我们现在召唤出了一种人类难以理解的非人类、非生物智能,它有可能逃脱人类的控制,除了可能危及人类物种的存亡,更有可能将无数其他生命形式也卷入危险之中。我们所有人在未来几年所做的决定,将决定召唤这种非人类智能究竟是个致命的错误,还是会让生命的演化翻开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篇章。
不容否认的是,尤瓦尔·赫拉利已然是当下最具影响的作家之一,这得益于他的千万册畅销书《人类简史》(《人类简史》迄今为止已售出2500万册),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二十一世纪托马斯·潘恩。然而,简单地将尤瓦尔·赫拉利看作是科普作家或者通史家并不恰当。在《人类简史》之前,他还有写作三部关于中世纪骑士的学术专著,《文艺复兴时期的军事回忆录》(Renaissance Military Memoirs: War, History and Identity, 1450–1600)、《骑士时代的特种作战》(Special Operations in the Age of Chivalry, 1100–1550)、《终极体验:战场启示录与现代战争文化的形成,1450-2000年》(The Ultimate Experience: Battlefield Revelatio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War Culture, 1450–2000),类似于年鉴学派的新史学。在其中,尤瓦尔·赫拉利的写作形态便已固定,相对于常规的学术著作,他会涉及更高密度的知识,为了平衡,他会在叙述上加入更多的启示感。
2011年先由希伯来语出版的《人类简史》,源于他为本科生开设了《世界史概论》。正如赫拉利几乎离不开“新自由主义”及其批判史,他本身更像是某种“新自由主义”作家,也就是建立在知识大爆炸与媒介“套娃”的基础上的新的想象与叙述方式,这与现代主义的精神史焦虑或者后现代主义的改良之爱大异其趣,当然也并非国内普遍误解为的与互联网“零距离”。赫拉利有至少三种我正在学习的某种技能,1)与冥想或者呼吸有关的,非书卷或者非手指写作,该怎么命名好呢,心灵写作吧;2)建立在严格的知识与学术意味之上的全景概览;3)双重下判断,带有趣味关爱与探讨的。
在牛津大学就读期间,尤瓦尔·赫拉利由于文化冲击和气候差异,陷入焦虑,朋友建议他尝试冥想,他认为这是幻术,遂作罢。一年后,尤瓦尔·赫拉利回神尝试,他惊讶于冥想效果奇佳,且相当科学,自此,冥想进入了尤瓦尔·赫拉利的每日清单。没有冥想,就没有后来的“畅销书”,尤瓦尔·赫拉利亲口承认。的确如此。冥想使我们排除不必要的干扰,清理混杂的思绪,帮助我们专注于重要的或者意想不到的事物,从而引导我们深度思考。读者对尤瓦尔·赫拉利的折服与共鸣,与其说源自“讲故事”,不如说源自冥想。事实上,尤瓦尔·赫拉利未必是讲故事的高手,却是传情达意的高手;未必是论述的高手,却是下结论的高手。
年轻时,贾雷德·戴蒙德(Jared Diamond)的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:人类社会的命运》(Guns, Germs, and Steel: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)使尤瓦尔·赫拉利颖悟,原来自己也可以写这样的书。大约十年后,他就兑现了这个期待,接连推出了几部简史:《人类简史》(Sapiens: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)、《未来简史》(Homo Deus: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)、《今日简史》(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)、《智人之上》(Nexus: A Brief History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from the Stone Age to AI),在人类的真相的“普遍的工程”上,留下了自己的痕迹。









 冀ICP备15028771号-1
冀ICP备15028771号-1